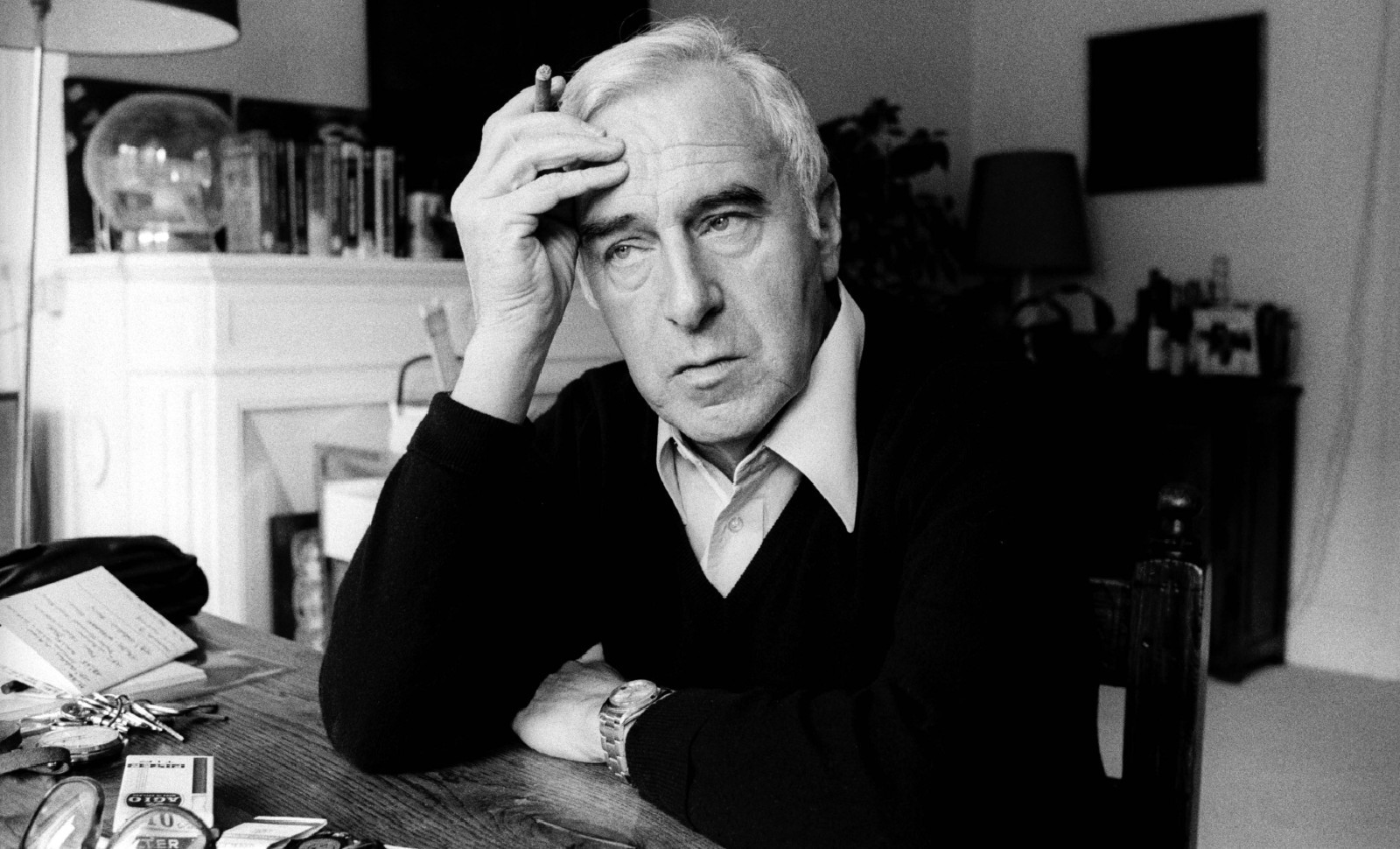【KFF 影展專書】《獵人兄弟》:觸不到的界線,在夢洄中徘徊
文/娜塔 ▪ 編輯/路宗恩 ▪ 核稿/游千慧
|
|
部落土地糾紛的真實映射
導演談到故事的緣起——在一次過年的家群聚會,長輩因為土地的關係打起架來,所有人都上去勸架,讓年幼的蘇弘恩印象深刻。長大之後,此類事件仍時有耳聞,讓他覺得可以寫一個這樣的故事。田野調查期間,他也去問過花蓮的朋友,如果地方遇到較大的開發案,會需要整個部落的人投票,其中有很多的操縱空間,「但就跟家庭紛爭一樣,總會有人犧牲,有人受益。所以這個故事大體而言,是建基在真實事件上。」
從《靈山》、《土地》直到這次的作品,蘇弘恩的創作穩定而扎實地望向自己所處環境的變化。蘇弘恩表示,《獵人兄弟》參考了《歸鄉》(The Return, 2003)、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《新居風暴》(The Salesman, 2016)等片,他很欣賞這幾部戲描寫家庭衝突的處理。「我自己希望在這樣的故事中,再多放一點文化背景進來,能夠跟其他作品做出區別。一直以來,我都挺喜歡長鏡頭跟場面調度,我覺得時間的流動對影像來說很重要。」
當代原住民的身份迷惘
隨著現代社會對居住和共同體概念的重新審視,山居生活與平地文化的交流呈現出愈來愈多樣化的面貌。面對這種變化,蘇弘恩導演對原住民題材的創作有著獨特的見解:「過往原民前輩的控訴、對外抗爭的作品,這幾年都比較少見。我這一輩的人,大部分會把重點放在『我是誰?我要去哪裡?』這樣的提問上。」他坦言,「大家對自己的身分都滿迷惘。我們過著太像平地人的生活,接受的教育也都大同小異。所以我也還在找尋新的可能性。」
《獵人兄弟》與近期上映的日本電影《邪惡根本不存在》(Evil Does Not Exist, 2023)在主題上有著微妙的呼應。兩部作品都探討了都市與山間生活的對比,深入探索人的生存狀態和共同體的本質。值得注意的是,兩片的結尾都呈現了一種近乎虛幻的場景:人進入自然,卻在其中迷失。
這裡的「自然」不僅指實體的山林,更象徵了人性在自主與受制之間的掙扎。通過這樣的呈現,兩部電影都在探討人如何在複雜的環境中認識自我,以及面對日漸陌生的世界。

兄弟情與價值觀的碰撞
誠如這部作品直白的片名,《獵人兄弟》著墨於兩兄弟生存處境的流轉與交界——他們各自選擇的生活方式,反映著兩種俗世價值的鏡面。影片中對於兄弟情誼的糾葛刻畫,帶有濃厚寫實氣息,令人想起維斯康堤(Luchino Visconti)經典作品《洛可兄弟》(Rocco and His Brothers, 1960)。
蘇弘恩通過均衡的鏡頭語言和簡練的對白,勾勒出雙方的處境與潛在的價值矛盾:我們如何共同生活(還有,我們又是誰呢?)片頭離家上山的場景,隱約牽動了電影往後的基調——入山有其謹慎與肅穆,在山中要面對的危險,同時也考驗並調度著每一次朝向死亡的風險。人在生存過程中直面的恐懼與本能反應,是導演有意強調的主題。
「我覺得這部片的歷史設定會延續到未來,畢竟這樣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。」在林野間,舉槍、設陷阱、火烤獵物等鏡頭,以緩慢而紀錄式的手法呈現,讓觀眾感受到某種「原始」生活方式。這種生活方式通過兩兄弟的選擇,呈現出兩條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。
值得注意的是,《獵人兄弟》並未將新舊、原始與現代刻意對立,而是探討了蘇弘恩一直關注的議題:部落生活與他自身之間的距離。「父」的角色設定,似乎源自導演過去拍攝外公狩獵的經歷,呈現了一種既存在又正在消逝的原始生活,整部作品充滿了節制又時而掙扎的觀望。
隨著劇情推進,弟弟林正上山後,鏡頭開始更多聚焦於哥哥林祥的家庭生活。這種敘事安排讓觀眾彷彿也與山中生活產生了陌生感和隔絕感。蘇弘恩解釋,礙於拍攝時間的限制,他不得不在劇本階段做出取捨,減少了山上生活的細節,將更多時間留給山下的主線劇情。而片中女性角色默默承受的「承擔者」形象,某種程度有著悲調的刻畫。對此,蘇弘恩解釋道:「這也體現了我對家中長輩的觀察,太魯閣族是個以男性為重的社會,所以女性很多時候需要承擔照顧家庭、照顧長輩的工作,可能一般觀眾會覺得刻板,但這就是部落的現況。」
剪接重塑與開放式結局
在後期製作中,剪接師滕兆鏘(曾負責《迴光奏鳴曲》的剪接)對劇本進行了大幅調整,重新講述了這個故事。「我覺得比我原來的結構好,特別感謝他。」蘇弘恩說。影片採用了開放式結局,「大家看了都有不同的想法,我也很喜歡這樣,觀眾的價值觀會影響對影片結尾的看法。我自己心中的解讀,是個比較悲傷的結局,所以在最後的配樂,走的還是悲劇的基調。」
作為觀眾在真相呼之欲出的結尾,我們能感受到影片呈現的張力:雖然有罪行的指認,《獵人兄弟》卻並不急於追緝。相反,影片幻入山林間的行進,強化了持續存在的「隔閡的不安」,直到內爆,情感顯得飄渺。結尾給觀眾留下的印象,像是在巨大的寫實日常中走入夢的殘響餘韻。